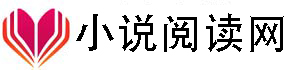30-40(9/39)
提了两大兜子药,想问问他的病情,突然就有点难为情,说不出话来。楼月自闭地回到卧室,把身上的羽绒服脱掉,挂在椅背上,然后蹲在行李箱面前,心如死灰地发呆。
她的卧室开着一条巴掌宽的缝,赵应东礼貌性地敲了三下后,推开门问:“我能进来吗?”
楼月脸贴着膝盖,指尖触地,奄奄一息。
赵应东把她的感冒药放在桌子上,也蹲下来,微小的气流滑过楼月的裸露在外的皮肤。
“六月十四日是世界献血者日。”她一言不发了很久,突然闷闷地说,“不信你自己去查。”
她的鼻尖卡在两个膝盖间的缝隙里,眼前是干净光滑的地板。
赵应东的手突兀地出现,松松垮垮地握着拳,随后在楼月眼前绽开。
手心是牛教练送给他的糖,楼月早就吃掉分给自己的那一颗了。
她看着那颗糖,烦躁地转了个身,脑袋朝床边,继续蹲着。
真像朵蘑菇。
赵应东不依不饶把手送到她眼前。
楼月:“你烦不烦啊?”
“不烦,你呢?”
“我很烦!”
“要玩一局连连看吗?”
楼月腾得站起来,一脚踹在赵应东的屁股上,他纹丝未动,她自己的拖鞋倒是因此甩了出去,脚趾痛得小腿都要抽筋。
“你去吃药吧行不行?”她踩在赵应东的背上,“能不能别一直霍霍人。”
赵应东在房间里穿着一件单薄的针织贸易,被她这样踩着,背阔肌抽动。
这间房里有两个病人。
他和她争先恐后地发病。
赵应东发病就癫味儿很足,楼月发病疯味很足,两个人轮流当凶手、当病人、当受害者。
只是楼月在角色转变时,状态差异很大,赵应东则是自始至终都很平静。
“你让我吃吗?”赵应东昂起头,目不转睛地看着楼月,“我就是来找我的药。”
他的目光让楼月想起十七岁时,她起了水痘,一个人躺在床上,因为嗓子里的口腔溃疡严重,吞咽受阻,吃药也拖拖拉拉的。
赵应东每次都不耐烦地帮她整理好一切,拿着药和温水,站在床前,“快点吃你的药。”
十七岁一晃就过去了,她二十四岁才回忆出一点味道。
楼月又往他肩膀踹了一脚,“我让你吃你就吃?我让你别烦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变态?”
赵应东站起来,捉起楼月的手放在胸口,“你不知道原因吗?”
他攥着楼月的手腕,力度很大,“你能感受到吗?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这么亢奋,在一起的时候亢奋,分开了亢奋,看到人了更是激动。”
“我可以走一百步,甚至你要往后退的话,我还能走更多。”
“但前提是你要一直看着我走。”
楼月的手被禁锢,索性狠狠地拧了一把,赵应东还是面不改色。
“你不看着我,我就控制不了自己。”
楼月:“你说的和我有关系吗?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要走一条路?我为什么要一直看着你,你是人民币吗?”
她又拧了一把。
赵应东的表情阴沉,“我会让你看着的。”
他把楼月的手挪到自己脖子上,她的手掌自动适应了赵应东脖子的粗细。
“你掐这儿,用力掐。”
楼月想起自己几个小时前被那只手握着脖子,只恨自己手不够大,妒火烧心,两只手